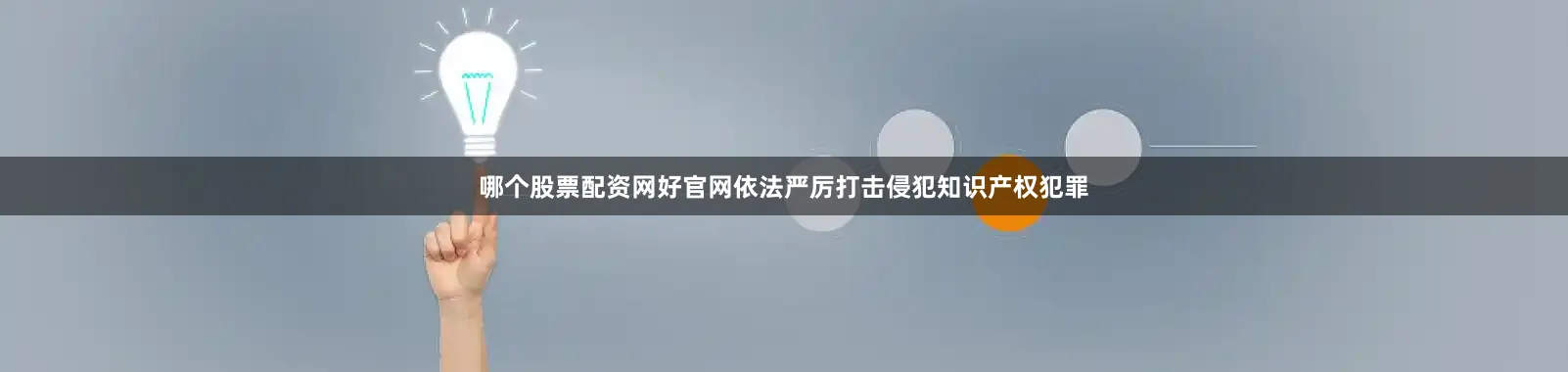1979年3月1日夜色压向黄连山腹地,雨丝在风口里横着飘。越军步兵316A师174团正忙着最后一次检查火力点,他们确信:四号桥这道狭窄关隘,能把中国边防部队挡在十号公路外。

四号桥不是普通的桥。十年前修桥时,越方就在河谷两侧凿出暗堡,火炮、机枪层层交叉。断面像一道喉咙,水深流急,一旦炸桥,对岸的进攻部队只能顺着裸露的公路爬坡,毫无遮蔽。越方公开夸口“天兵也难从此过”,口气嚣张,却也说明自知地形之利。
3月1日傍晚,我军50军149师的先头2营夜行至三号桥,误将其当成目标,踏上桥面时队形松散。敌暗堡突然点亮,机枪交叉扫射,几秒钟火网压住桥面。我军措手不及,首尾难顾,二十余人当场倒下。
混乱中,营部迅速抢占东北侧一座无名高地,几挺重机枪对准桥头,以火力掩护残部脱离。高地虽然不起眼,却刚好卡在河谷折线处,挡住敌侧射,这一顶,给后续硬攻争来宝贵二十四小时。

折翼的2营被紧急撤下。营区包扎间灯光昏暗,担架一排排摆到泥地上。在场的卫生员后来回忆:“雨水和血混在一起,只能靠体温分出死活。”那一夜,149师高层意识到,必须把进攻节奏从“步兵摸过去”改成“炮火撕开口子”。
天亮前,师里下达新命令,1营担任主攻。连长鲁宝成把地图摊在湿篷布上,低声叮嘱各排骨干。排长周从连回头给战士们打气:“硬啃,别磨蹭,打出缺口就是活路。”一句话,把憋屈的火气瞬间点燃。

3月2日04时,山谷炸雷般轰鸣。149师炮团破例把122榴弹炮推到距桥不到一百八十米的位置,抬炮、急速射——严格意义上,这已跨过“安全界”。炮口火舌把黑夜撕出一道道白痕,桥头暗堡被掀翻,钢板卷曲。炮兵参谋刘中林后来苦笑:“那会儿只管把敌人压趴,再近也得顶。”
硝烟尚未散尽,1营战士借着炮火掩护跃出河岸。冲锋号没有吹,脚步声和雨声混在一起。副连长朱国端着冲锋枪冲在最前,可惜一粒流弹划破雨幕,击中他的头盔边缘。倒地瞬间,他拉住一名战士嘶吼:“别停,往前冲!”话音未落便再无呼吸。
桥面被我军爆破破开豁口,敌残余火力仍在两侧山腰负隅顽抗。149师政委孙××索性带着高射机枪班闯到最前,把机枪架在碎石垛后,点射压住山腰明火点。他对身旁警卫员怒吼:“挡着我视线?滚开!”几乎就是硬把阵地生生推前了几十米。

与此同时,445团两个连从侧翼沿河谷攀岩而上。雨天石面滑,战士们用刺刀撬着岩缝,手掌磨破也咬牙不松。副军长刘广桐神色铁青,站在公路边亲自指挥——将军顶到步兵第一线,很少见,却在此役成了常态。
上午八时许,桥头敌火点大部被摧毁,1营突入桥头阵地。不到十五分钟,第一面红旗插在桥北侧凸起岩石上。敌人见势已去,向沙巴方向仓皇后撤,留下满地弹箱和被烧得扭曲的迫击炮。

战斗结束统计,1营减员三分之一,其中半数是在冲锋最后两百米被流弹击中。医疗排冒雨往后方抬人,最远的救护线依然在四十公里外的浮桥。因路况恶劣,不少重伤员颠簸两昼夜才抵达国内医院——这条补给线的艰难,后来成为研究越南北部山地作战的反面教材。
四号桥拿下后,149师乘胜沿十号公路直插沙巴县。刘广桐干脆跳上突击队的59式坦克,坦克驾驶员愣神,他大喝一句:“快踩油门!”钢履带碾碎残余路障,十余分钟直抵县城边缘,把敌守备分队吓得四散。
从3月1日至3日清晨,四号桥争夺战历时不足四十八小时,投入兵力不过数个营,却打出了全线推进的突破口。越军早先的豪言化作焦土,而149师“炮火顶到脸上”的打法,也在友邻部队口中成为不折不扣的“广西风”。

随后的总攻中,我军边防部队沿线推进二十至四十公里,相继控制谅山、高平、老街等要点。3月5日,作战目标完成,部队开始有序撤回。四号桥一役虽小,却像一枚楔子,把越军王牌师精心布下的山地防御体系撕开。士兵们常说:那桥头上的石块,至今还残留火炮震出的焦痕,这才是真正的“铁证”。
趣富配资,同花顺配资,最新股票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